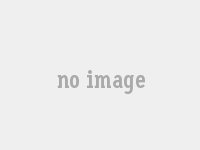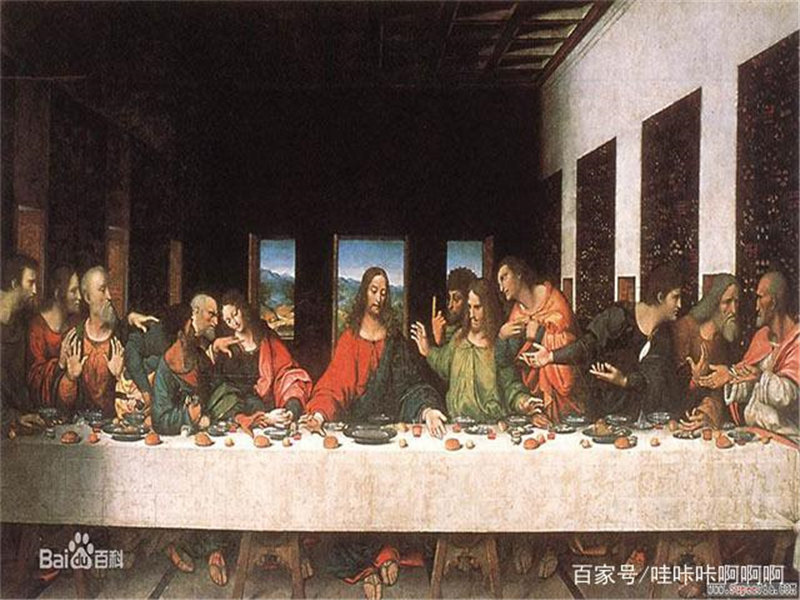现象学哲学创立者胡塞尔不仅拓展了欧洲的思维方式,也关注欧洲之外的思想形态。根据卡尔·舒曼的考察,胡塞尔在1925—1926年冬季学期的讨论课上专门探究过佛教问题,遗憾的是没有留下详细课程记录。不过,他写了两篇文稿:《论〈觉者乔达摩语录〉》(1925)和《苏格拉底—佛陀》(1926)。对与现象学哲学相关的东方思想有过思考,并用三种方式描述了佛教对世界的理解。
第一种是“宗教—神话”的描述方式。佛教的原始典籍大多是以神圣故事作为开端的,胡塞尔起先认为,佛教解释世界的态度是“宗教—神话”式的,这与欧洲哲学解释世界的态度截然不同。“宗教—神话”式的思维类型并不是一种诉诸普遍理性的类型,而是一种建立在“纯粹经验的人类学上的类型”。而欧洲哲学的态度,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希腊—欧洲思维类型,则具有绝对理论洞察的科学理性精神。两者并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对世界进行观察和认识。
胡塞尔志在从事具有普遍意义的严格科学的哲学研究,并且特别专注于其所从事的哲学是否能够保存自身等问题。而带有“宗教—神话”态度的人只能依靠与神话相关的神秘力量,其在广泛的意义上往往被理解为某种人格的精神力量。他们的目光总是指向被神秘力量所决定的世界。因此,胡塞尔认为,佛教的目的虽然在于尽可能幸福地安排世间生活,但并没有以科学的经验来认识事实世界。
第二种是“宗教—伦理”的描述方式。第一种方式基本上是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佛教的,而“宗教—伦理”的方式则用肯定的语调阐明佛教在实践方面的价值。胡塞尔写道:“佛教显然是关于心灵净化与祥和的一种最崇高的宗教—伦理方法,它以一种内在一致性去思量和践行,达到一种几乎无可比拟的能量与高贵心境。只有我们欧洲文化中最高的哲学与宗教精神才能和佛教相比。”他所说的“最崇高的宗教—伦理方法”就是佛教的修证与解脱之法。胡塞尔认为,这种精神修习的工夫有着指引作用,能够获得一种自在有效的真理。
《法华经》中有言:“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生悟佛知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知见道故,出现于世。”也就是说,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伦理”的实践修行,既需要典范人物的开示,同时还需要自身心灵的纯粹性和纯真性,如此才能将其建立在对绝对实践真理的明察之上。因此,胡塞尔认为,佛教虽然没有像基督教那样去处理“人神关系”,但却在伦理实践中处理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第三种是“宗教—哲学”的描述方式。与“神话”和“伦理”不同的是,胡塞尔的“哲学”描述方式更多地关注着现象学哲学与佛教义理之间的异同。现象学虽然一开始是以认识论形态登上历史舞台的,但到了胡塞尔后期,他更关心的是如何论述现象学在实践功能方面的作用。胡塞尔在《论〈觉者乔达摩语录〉》中说:“我们的命运就必须要以印度的新精神道路与我们的旧方式对照,并在这对照中使我们的生命重新活跃和强化起来。”
西方的佛学研究直到19世纪才开始起步,研究方式以古典语文学与实证史学为依托,对佛学原典进行整理、校勘、翻译、诠释,从而形成其固有的一套典范模式。古典语文学与实证史学的思路固然有助于客观了解异质文化,但其弊端也显露无疑,即只重视语言文献方面的单一操作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哲学对话或义理解悟。胡塞尔的解读方式与古典语文学和实证史学不同,他从思维形态出发来跨文化反思欧洲与印度的异同,从而能够站在哲学对话的层面进行描述。
胡塞尔对佛教的“宗教—哲学”描述可细分为四点。在义理构型上,佛教与现象学哲学相似,都摒弃了对自然态度的基本信任。因此,佛教所采取的也是一种“超越论的”立场,这种立场与现象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思想方法上,佛教与现象学具有“同构性”,都使用了还原方法,悬搁了一切超越的设定。佛教废黜了客观的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重视普全出世的意愿,上达圣道,下化众生。在态度风格上,佛教与现象学存在不同。佛教总体上屈从于一种“非理性”的态度,而属于欧洲传统的现象学哲学是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的,“非理性”的生活要受到理性规范的支配。在终极目的上,佛教的目的在于内在解脱,达到人生最终意义的精神圆成,而胡塞尔现象学的目的是想建立一种严格科学的哲学,在人生的意义问题上关注较少。当然,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也指出,新任务是通过行动来证实现象学哲学的实践功能,以此追问“关于这整个的人的生存有意义与无意义的问题”。
胡塞尔的最终目的是希望人类转变成“能够依据绝对的理论洞察而绝对自我负责”的新人类。而这种目的就存在于“第三种方式”之中,一方面与“宗教—神话”和“宗教—伦理”的态度相对,另一方面又与一般的理论态度相反,它是“以一种新型实践的形式实现的,以对一切生活和生活目的,一切由人类生活已经产生的文化构成物和文化系统进行普遍批评的形式实现的”。这是一种综合了实践态度的理论态度,亦即胡塞尔所说的“新型实践形式”。在这个基础上,理性不再区分为“理论的”、“实践的”、“审美的”等诸多方面,而是将自己理解为处于其理性的全部生活中的科学存在,“将自己理解为有责任过一种具有必真性的生活的存在”。胡塞尔所提出的这种要求,实际上在他论佛教的两篇文稿中已可见端倪。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