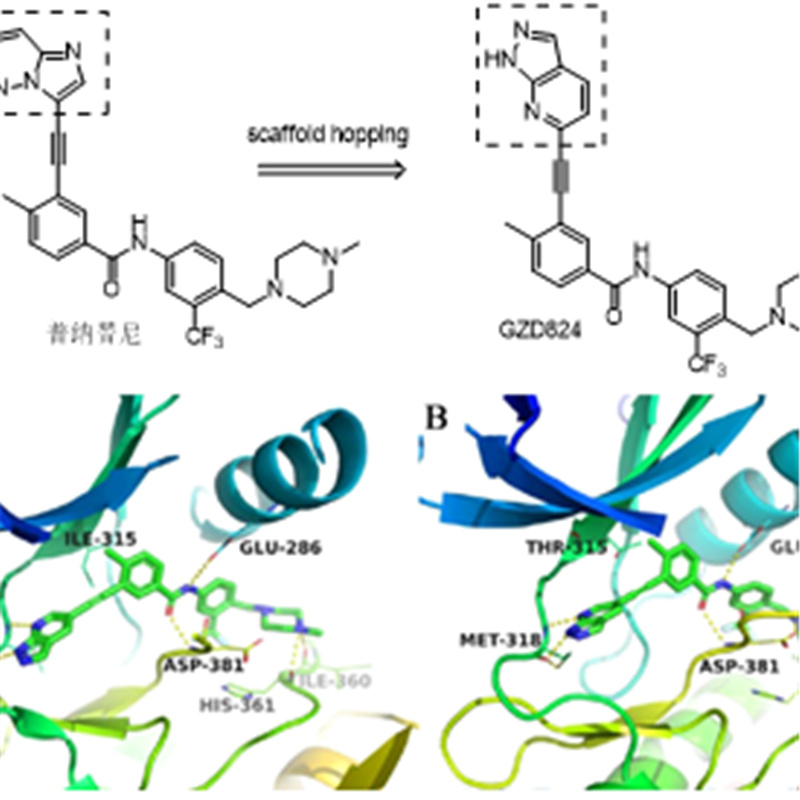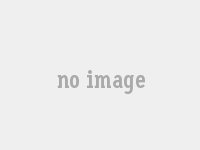编者按
2017年的国际环境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执政、欧洲多国选举、英国脱欧启动等重大事件给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带来了剧烈的变化,各国的经济政策走向也将发生深刻调整。
站在历史的拐点,发达国家的政治局势和经济政策将如何影响世界?我国将如何看待全球经济的长期发展中面临的风险、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政府将有哪些政策选择?这些问题对于维持我国长期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在上海举办的浦山基金会首届年会上,本期圆桌嘉宾对上述问题展开了如下探讨。
嘉宾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朱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管涛 浦山基金会理事、CF40高级研究员
主持人 潘英丽
全球经济正面临一系列的拐点
中国经济时报:世界经济的现状处于低迷状态,经济结构正在调整和变化当中,我国应如何去看未来世界经济的变化?
朱民:从结构变化来看,我认为世界经济正在面临拐点。一个拐点是,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强势美元。特朗普政策改变了市场预期,货币市场汇率波动在不断地加大,全球利率发生了变化,这一政策成为推动目前经济金融的一个重要拐点。随着利率水平的调整上升,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开始上升。另一个拐点是,美国财政政策拐点。由于受到政治影响,美国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加大,而民粹主义的兴起和政治风险也面临拐点,这将成为全世界政治变化的又一个拐点。总体看来,未来10年全球经济正在发生一些流动性拐点、财政政策拐点,以及政治拐点。政治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将会成为主要风险。全球经济增长波动、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以及全球经济金融将再次受到调整。
我认为,尽管世界经济出现了一系列的拐点,也会不断地影响未来经济金融结构性的变化,2017年可能略有上升,但整体仍在下行,全球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与此同时,受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全球真实利率持续下降。低油价、低进口不是危机,而是均衡的状态。
中国经济时报: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我国未来经济将面临哪些挑战?
余永定: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结构变化密切相关。英国经济学家克洛舍(GeoffreyCrowther)把国际收支格局变化分为六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都有不同的特点。从国际经验看,直到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年轻债务国。但是经过一个阶段之后,又恢复到原来的情况,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
中国国际收支结构与标准模式和其它国家完全不同。从一开始,中国就是经常项目顺差,并且是净资本输出国,即净债权国。最近几年我们发现,中国的净资产并未随经常项目顺差的积累而增长。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呈现出长期双顺差和外汇储备日益积累的特征,并且存在五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在人均收入400美元时就是净资本输出国,保持大量的贸易顺差。第二个问题是,作为世界第三大引资国(FDI),中国所出售的股权被转化为美元债权,而不是转化为进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储备资产(双顺差的累积)的价值面临美元下跌的威胁。第四个问题是,中国的净资产收益率是负的,最近10年这个问题尤其突出。第五个问题是,资本净输出并未转化为海外净资产,尽管依然保持着经常项目顺差,但是海外净资产却并没有增加,这似乎是独特的中国现象。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未来世界经济结构性变局将出现哪些变化?
朱民:过去8年多,发达国家的投资下跌GDP的25%,投资下跌,经济增长只能靠消费推动。当整个经济轻化时,国内投资必然会减少。很重要的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和影响非常大,我们对未来GDP的潜在增长预测分为资本的潜在增长率、劳动力的潜在增长率和劳动生产力,而现在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劳动生产力增长水平下跌幅度较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增长水平压到了很低的水平,经济增长的水平也降了下来,这是非常大的结构性变化,也成为了今天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
从全球已经出现的一些趋势性变化来看,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全球经济继续“轻化”。全世界出现服务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轻资产变得越来越重要。当世界变“轻”的同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收入对贸易品的需求弹性也在下降。在过去10年里,人们不再需求丰富的从国外进口的物质产品,转而消费更多国内的服务业产品。这成为全世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对消费服务业的需求变化。
另一方面是全球人口不断增长,2016年是74亿人口,2100年将是110亿。从人口结构变化来看,全球劳动生产力结构正从GDP增长人均高的地方转移到低的地方。另一方面是美国人口迅速老龄化。美国65岁以上人口占15到65岁劳动人口比重,2015年是22%左右,2025年比重可能达到32%左右,将增加10个百分点,它改变了劳动力的供应结构。如果2050年美国年轻劳动力人口增长速度下降,将在根本上改变未来全球经济金融基本格局。
中国经济时报:根据这些变化,新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点在哪里?没有新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如果人口持续地老龄化,将用什么财富来支持未来老龄和社会人的需求?我们用什么来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均现象?
朱民: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对所有人来说是一个巨大迷思,也是经济、政策、社会的一个巨大挑战。在未来的10年,寻找劳动生产率新的增长点,是第一等要事。所有的问题,都必须从提高这个水平找到答案,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我国应理顺国际收支结构
中国经济时报:一个国家随着经济的增长,国际收支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看到,中国外汇储备在2014年达到近4万亿美元见顶后开始下降,现已下跌至3万亿美元左右。请谈谈对该问题的看法?
余永定:我认为,中国国际收支结构存在的问题已经不容小觑。按道理,2011年到2016年期间,中国的海外净资产应该相应增加,但中国的海外净资产不但没有增加,反倒减少了,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由于中国汇率长期以来缺乏灵活性,尤其是2012年后中国资本项目开放过急、过快。在低汇率下,贸易顺差急剧增加,而人民币在该升值的时候没有升值,导致升值预期愈加强烈。从2005年起,在高回报率和升值预期的驱使下,大量热钱急于流入中国,进而导致中国国内资产价格上升。另外,中国资产和负债存在结构不合理性,虽然中国是资本净输出国,但海外投资收入为负。如果不能把国际收支结构理顺,老龄化来临后,我国能否像日本那样享受投资收益,或在我国贸易顺差不能维持的时候依然能够坚持贸易顺差,从而获得外汇还债、支付利息,将在未来面临巨大的挑战。
管涛: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对资本流动的管理,但在2013年美联储提出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前,应该说新兴市场国家主要管理的是资本流入冲击的风险。不仅是新兴国家,我们看到,发达国家也开始考虑宏观审慎的管理问题。
从非银行部门来看市场,在企业和家庭的跨境收付里,2016年全年,人民币在跨境收付占比中下降,下降的比重绝大部分重新回到美元上。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很有可能在整个市场的外汇收支活动中是一个重要的价格信号。我们看到2016年实行参考一揽子货币调节,有管理的浮动,当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的时候,外汇供求关系是改善的。下半年,随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了比较大的调整以后,外汇供求关系恶化。2017年伊始,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的人民币汇率,都出现一定程度的升值,在这种情况下,境内外人民币的汇率差价重新出现倒挂。
应加强我国对跨境资本的管理
中国经济时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加强我国对跨境资本的管理?
管涛:我认为,首先在不违反国际规则前提下,应加强我国对跨境资本的流动管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定,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八款义务,取消经常项目对外支付和转移限制,是基金组织成员的一般义务。甚至在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反对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管理,只要这种管制不限制经常性国际收支交易的资金转移,就不违背第八条款。
对中国而言,在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上,以及与国际规范接轨方面,也进行过一些实践。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当时中国政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同时要保持外汇储备水平的基本稳定。那种情况下,主要通过加强和改进外汇管理,应对资本流出的冲击。对当时的外汇管理最大的约束就是,我国在1996年底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而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初期,出于比较强烈的贬值预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资本外流,主要方式是以进口骗购外汇的方式,对外转移资产,造成了贸易大量顺差,但又有贸易顺差逆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国在跨境资本流入的管理上尝试了宏观审慎的措施,也就是所谓的托宾税措施,意味着银行不能按照利率平价,要把风险敞开定价之后,加入远期价格里,进而影响市场的结售汇行为。
我个人理解,这个宏观审慎的措施就是托宾税的做法。托宾税不一定是税,是基于价格的手段调节跨境资本流动。调节跨境资本流动,除了一些行政管理的手段,更要重视市场价格信号的作用,通过汇率的波动促进市场。另一方面,汇率本身不论是固定还是浮动,也起到市场价格信号的作用。所以人民币对美元的双边汇率,有可能在整个市场的外汇收支活动中就是一个重要的价格信号。
中国经济时报:在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方面,你有哪些建议?
管涛:可以用市场手段调节居民个人用汇。比如服务贸易下的购汇,2016年其它的用汇基本上是同比负增长,唯有这个项目是同比正增长。无法提供用汇证明的,或者明确用于海外投资目的的用汇,也可以采取价格的手段。比如收取一定的费用来减少有贬值预期的资产重新配置的动机。其次,可以考虑更长远的以金融交易税的安排去调节跨境资本流动。这是很多拉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做法,是一种托宾税的制度尝试。
在对外的证券投资方面,可以征收一定的税收,但要交一定的费用,通过价格手段起到调节的作用。另外,我国对外放款也可以用价格的手段调节,但是成本要提高。通常来说,金融交易税征收的对象应该是短期资本流动,但我们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的变化。中国在“8·11”汇改前后,每个季度的ODI项下的净流出大幅增加,短期内以及时间点非常巧合的情况下,出现这种飙升,可能就不太正常了。
我们可以看到,有关部门对于国内企业在海外并购,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采取了一些规范性行政措施,是否可以考虑采取金融交易税的做法,对长期资本流动也进行征税。当然,未来如果形势变化,金融交易税不仅可以考虑对流出征税,也可以考虑对流入征税,以避免政策在行政管理方面出现反复。
我建议,中国将来也可以和相关国家,特别是主要的国家建立正式安排后,从反避税角度,对跨境资本转移进行相关管理和外汇管理结合起来一并操作。
刚才说的都是比较初步的想法,操作过程中有些技术问题还需要解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宏观审慎措施和行政手段相比,容易形成政策反复和一刀切,通过价格手段影响交易成本,相对更加可行。任何资本流动的管理措施,都不可能替代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只能为改革和调整争取时间。